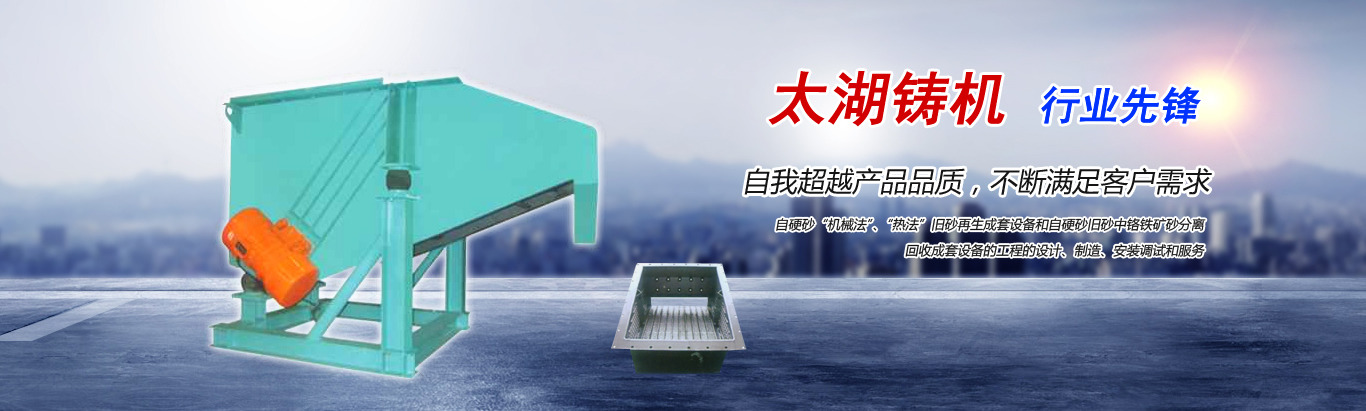机器人建造助高迪的圣家堂加速建设
时间: 2024-02-13 09:50:34 | 作者: 典型案例
“机器人建造”是当今建筑学的热门线年在维也纳举办的第一次RobArch会议以来,仅仅五年的时间,“机器人建造”在全世界内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着。随着这几年机器人装置的数量几乎呈指数增长,如今的“机器人建造”已经在创意产业中达到了井喷式发展。
建筑师对机器人劳动的幻想在上个世纪就已开始呈现,最早可溯源到法国艺术家Villemard在1910年发行的明信片中表达的乌托邦式愿景。后来英国建筑师Ron Herron在1964年提出“行走城市”的概念。20世纪80、90年代,日本建筑行业开始使用高度定制的机器人进行高层建筑。
机器人在建造中的使用,最早可追溯到1980年代。相对于Villemard明信片中显示的高度分化、各司其职的机器人,以及日本使用的单功能高度定制机器人,现在的机器人更倾向于多功能、灵活性和适应性。现代数字建造先锋F. Gramazio和M.Kohler对机械臂的实践研究进一步证明了,机械臂不仅仅可以类比人类手臂,还可以执行超出人力范围的建造过程。而飞行机器人更是突破了人类不能飞的局限,尤其是在空中自由操作的能力。
在古代,建筑大师(Master Builder)是人们对建筑师的称呼。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《建筑十书》里提到,建筑大师的工作范畴应涵盖工艺和理论,他认为完全依靠理论而忽视建造工艺的建筑师,所追求的是幻影而不是实际。由此可见,传统的建筑生产模式对建筑师的期待乃是非常精通建造工艺的人,而这一个角色在当今的建筑师身上已特别难找到踪迹。
建筑是基于物质材料的实践学科,其最终实现缺少不了真材实料,也不能抛开将材料加工组合的技巧。这决定了选材和制造是设计过程的本质。因而传统模式的建筑师无法脱离建造的角色。
而在工业革命后,由于时代对批量生产的期待,更有效率的流水线工作模式需要对分工进行细化和专门化,从而设计师与建造师的角色也渐渐被分离,建筑师逐渐脱离了把设计“物化/变现”的过程。这种建筑大师们没办法理解的工作模式,在工业革命的时代大背景下却是大受追捧。Joan Soane爵士就是力捧建筑师角色纯粹化的第一人。
事实上,建筑大师角色的瓦解一度给社会带来强烈的不适。建筑大师消失后,两个新生的职业开始盛行:一是只负责设计、但对建造没有真正了解的建筑师,二是只负责建造、而对设计没有真正了解的施工承包商。当设计师不具备建造技能时,设计往往容易变成不现实的、昂贵的、超出预算的“漂亮图片”,对人民生活的真正需要也容易缺乏关注。
无论“流水线”模式如何被人诟病,在大规模建设时代,不可能接受建筑大师模式的生产效率。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,人类必须在建筑大师和效率之间找到一条出路。
而数字建造把建筑师重新带回了建造的角色中。数字化加工要求建筑师详知整个作品是如何建成的,甚至在设计的最初阶段就开始考虑建造。通过机器人对建筑师命令精确的传达执行力,建筑师又重新掌握了建造的全局。在数字建造的辅助下,建筑师再次有机会扮演一个建筑大师的角色。然而,现代的建筑大师无论是在构思方式上还是设计流程上,都和传统的建筑大师大有不同。
数字建造于20世纪上半叶就已开始在欧洲出现。数字建造之下的工作流程,简单地描述就是:人负责设计,计算机将设计抽象化为数字,机器人将数字物化成实体。人的设计转化成命令,而机器人则根据命令去建造。
这个流程的枢纽在于“命令”,命令是一个桥梁,可以精准地将人类的设计意图传达给负责执行的机器人,实现了建筑师和建造过程的直接沟通。而在这种工作模式下,建筑师的设计实际上也集中于设计生产的全部过程,多于设计图像或模型。
早期的数字建造采用的是传统的“自上而下”的做法,目标是使用电脑来实现建筑师的设计。建筑的形态依然是在一开始就设计,而计算机则是用于帮助实现和坚持设计的意图。
新倡导的数字设计方式则是“自下而上”:建造过程所涉及的每个成分(表面,材料,机器和模具等)都提供了一系列约束和潜能,例如:模具的选材会导致加工环境的变化,而不同的切削工具也会在模具上产生不同的效果…所有这些参数都为数字物质化提供了广泛的潜能。
这种设计方式使得建造成为设计的源头。它不仅仅意味着设计的最初应当充分考虑到建造的局限,更意味着建造过程有很多未被发掘的潜能将被发现。而这些潜能,在“自上而下”的设计中是很难想象得到,并加以利用的。
机器人加工的建设能力界定了设计的可能性,其优势所在的数字化生产模式启发了一种基于算法的设计策略。和传统的侧重表达形态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不同,运用机器人技术进行设计所得的模型,不仅包含了设计逻辑,还包含数字建造加工的过程。除了体现形态,还可以生成指挥机器人为其执行生产所需的控制数据。
“自下而上”的设计方法,要求建筑师对建造工艺非常了解。如果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能够即时知晓建造的情况,对改进设计将会非常有利。
设计与建造在建筑大师的时代,本是一个不断反馈、一直在改进的动态化互动过程:建筑大师们一边现场指导施工,一边随时调整策略。工业革命后,这种互动丢失:设计师完成设计后,建造过程才能开始。设计师需要在不知道建造过程的情况下完成设计,而建造方也不能参与设计。“流水线”模式的建筑生产使设计与建造互相脱节。而数字建造所拥有的反馈机制,则将设计与建造互动的可能性重新带到生产的全部过程中。
数字建造对复杂的建筑元件可实现实地加工,相比于承包给加工商可节省不少开支,更免去了运输的麻烦。然而,数字建造的门槛也很高:设计师需要懂建造,懂编程,还要懂操作复杂的机器。
2010年,两个奥地利艺术家为制造出红牛拱的铝拱,他们购买了一台KUKAprc机械臂,然而却不会使用。他们找到了建筑机器人协会。
建筑机器人协会的工作人员说:“考虑到艺术家们的预算情况,我们最终决定,与其将这单制作外包给协会,不如将机械臂的操作知识传授给他们。在四天之内,我们的工作人员教会他们机械臂的基本操作、Rhino和Grasshopper。尽管他们之前连CAD都不会,却很快对这些软件上手了。四天之后,他们已可以用机械臂进行泡沫切割。他们甚至自己尝试去改进加工。”
这个拱总共包含了84块零件,每件零件的形状都不一样。在学会相关操作技能之后,两位艺术家能轻松对形态设计做调整。无论他们更改了拱的高度、宽度或是别的什么参数,都能实时地看到这改变对建造过程产生的影响,而后评估自己的设计是否可行,再返回去继续调整设计。
这样的工作流程,实现了设计与建造的互动。设计影响建造,同时建造又返回来影响设计。在两者的互动中,方案得以不断推进和调整。
在艺术家完成泡沫模块切割后,所有的铝元件在德国铸造完成,2012年夏天,红牛拱在奥地利史皮尔堡完成了它的最后集装。能够准确的看出,有了实时反馈机制,实际建造过程变得可预测,相关应对策略也可以在设计阶段就制定完善。这让新一代建筑大师们即使不亲临施工现场,也对建造过程全面掌控。
数字建造设计是对生产的全部过程的设计,相对于传统设计手段留下来的图纸、模型,数字建造设计留下来还有整个建造实现过程。
位于巴塞罗那的圣家堂(Sagrada Familia)是高迪最有野心的作品。在高迪去世的时候,这个教堂只完成了20%,它是唯一一个未完成就被评为UNESCO世界文化遗产的建筑。截至今日,它已完成了70%。这个融合了高迪个人风格的罗马哥特式教堂极其复杂,工程量浩大,它的跨时代意义在于,见证了人类工艺水平从人力建造时代发展到数字建造时代。
高迪去世以后,圣家堂的建设首先由其助理接手,1936年西班牙内战之后,开始由其他建筑师负责。数字建造于1989年开始被引入圣家堂工程。在圣家堂当下的建设中,擅长数字建造的新一任总建筑师Mark Burry试图去追溯高迪对材料的实践成果,从古老的切石法研究到七个自由维度的机械臂切割。
圣家堂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的石头工艺。石头是人类所熟知的最古老的材料之一,然而也是非常消耗人力的工艺。高迪曾亲自测试过不少当地石材和进口石材的承重强度,教堂中心最高的四根柱子将达到172.5米的高度,只有极少石材能胜任这几根柱子的承重使命。
圣家堂所有的柱子都有1:10的宽高比,因而越高的柱子就越粗,一根14米高的柱子就由112块花岗岩组成。每块花岗岩有必要进行36小时的加工,由此推算,14米的柱子需要168天完成。然而,在这段漫长的加工时间内,机械臂所操持的锯轮只有1/3的时间和岩石接触,其他时间都用于调整自己的位置以寻找合适的切入角度。为了更好的提高加工效率,建筑师们决定将古代工匠的切石工艺编入数字加工流程中,让机器人按照古人的智慧进行加工。
数字建造对设计原稿的还原度之高,无愧于高迪的天才设计。而随着加工工艺的一直在改进,建设效率也会慢慢的高,圣家堂有望在2026年竣工。没想到,高迪对石头加工工艺的研究成果,通过机械臂的实践传承了下来。
然而更早的建筑大师们没这么幸运。许多宝贵的建设工艺没能赶上数字建设时代就已经失传。比如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(于1296-1436年建设)的穹顶,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砖造穹顶,在当时被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而对于现代人来说,即使建筑师流传下来的手稿解释了部分原理,其具体的架构过程也是个谜。
所幸的是,在数字建造时代,设计师们不再受传统加工水平的限制,设计获得了更多的可能性。而接踵而来的各式各样的建造工艺,都可以被记载入人类建造的大档案库。